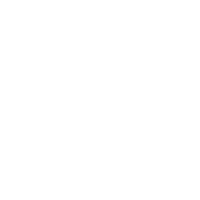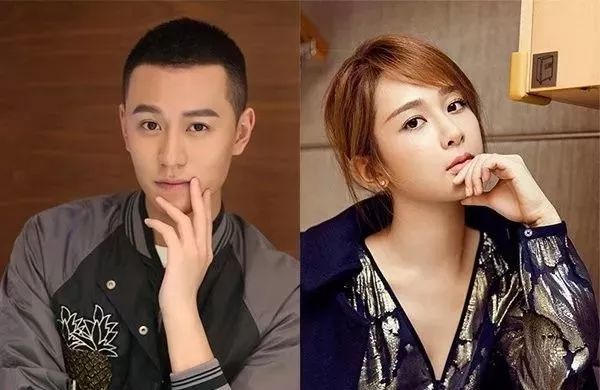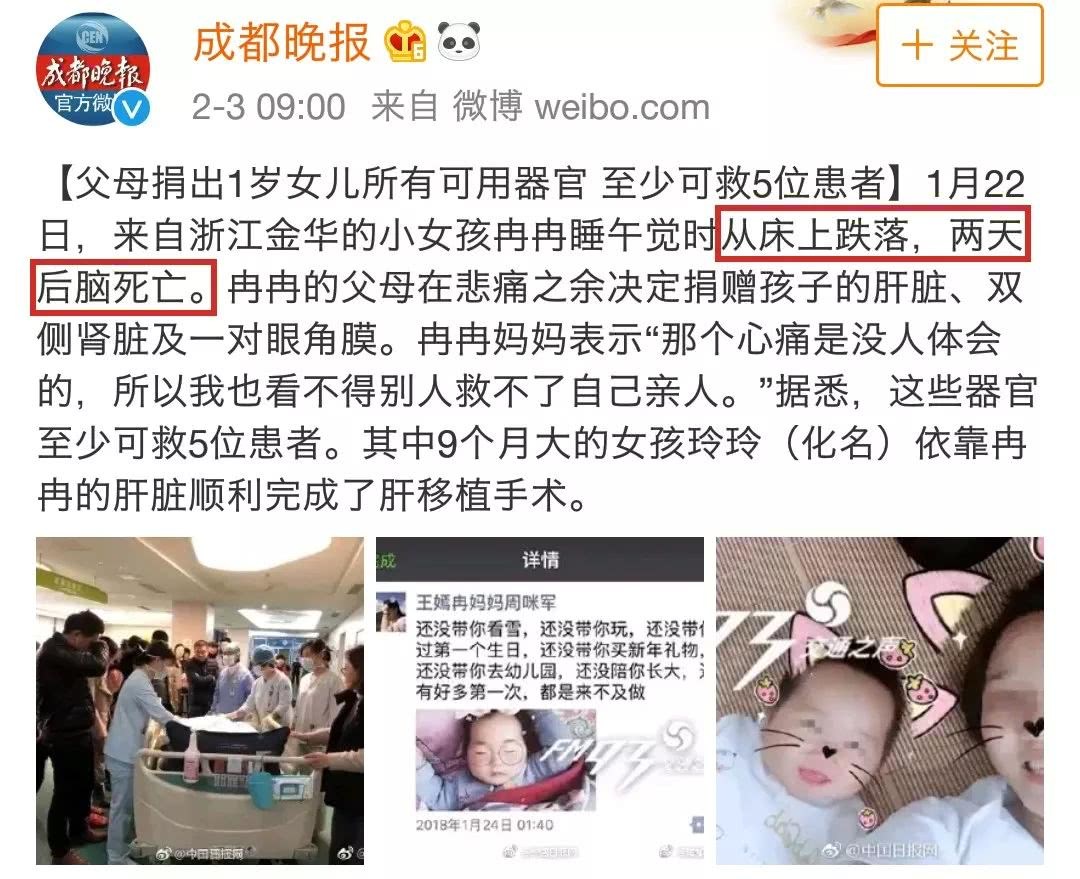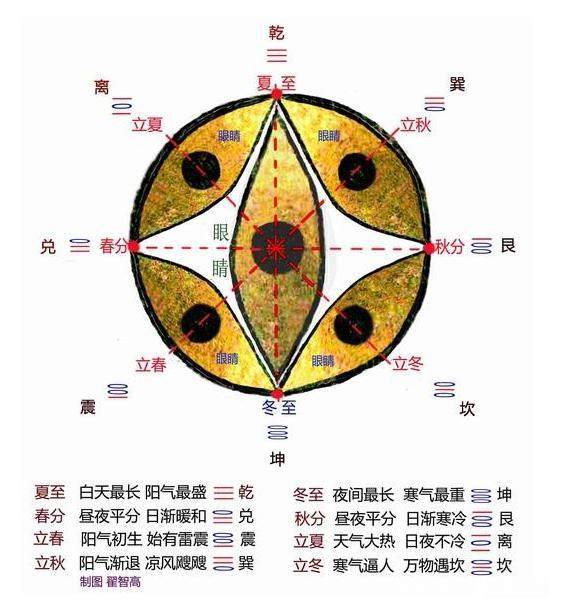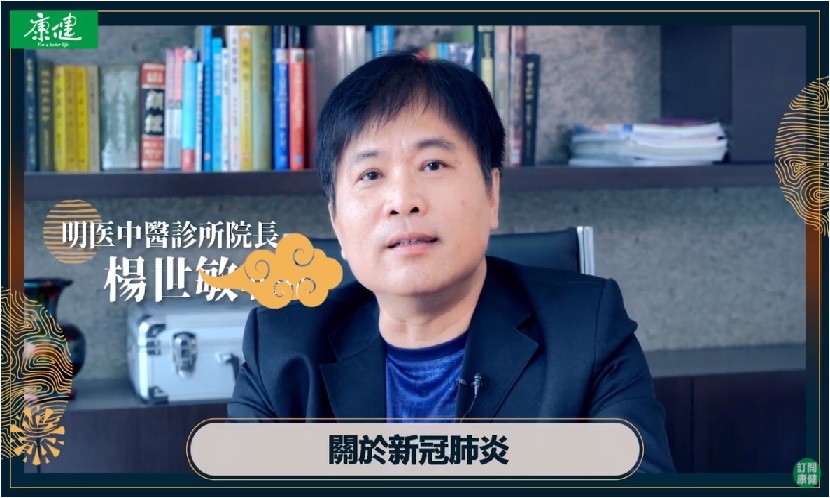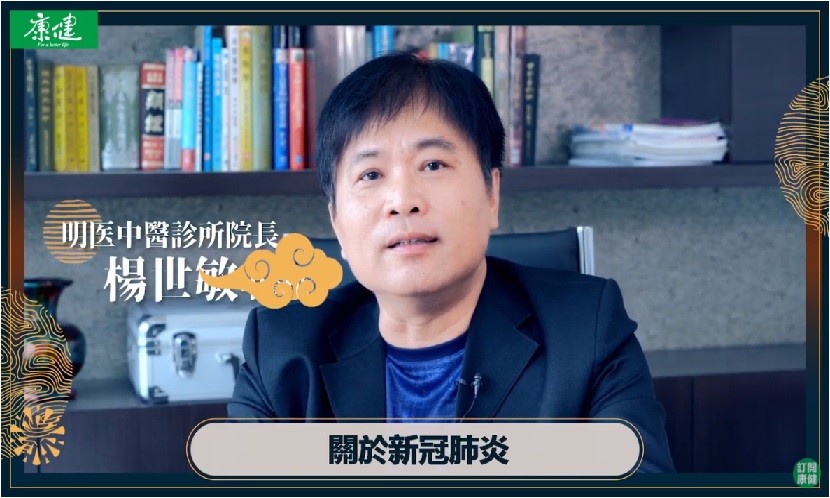但交给老师时,却对老师宣称这些孩子中有某些孩子是认知能力明显优于其他孩子的“资优生”,其他孩子则只是“一般生”。而在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重新再对所有的孩子们进行认知测验,却发现“宣称是资优生”的孩子们,表现明显较“一般生”要佳,且在年龄越小的班级差异表现得越大。显示了他人对于孩子的预期表现,将影响他人对孩子所做出的努力及付出,也就是心理学中著名的“毕马龙效应(Pygmalion Effect)”(Rosenthal & Jacobson, 1968)。
毕马龙效应,重要他人与孩子表现交互影响的操弄师
为什么对孩子的预期表现会造成影响孩子表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心理学家认为,当人对孩子有了预期,人就会在自己的行为模式上出现自动调整,借此让自己的预期成为现实,形成了自我验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Merton, 1948)。
也因此,当老师被灌输了“他们是资优生”的预期后,自然便会对于孩子有更多的引导或是提供更多的资源以符合“资优生的需求”,进而导致“宣称的资优生”最后真的变成“资优生”的结果。而这样的效应,显示了在儿童发展领域,无论是老师、照顾者或是各专业,对于孩子的预期【请注意,是“预期”而非“期待”】是有多重要。然不可讳言的,在现今社会的我们,很容易对于孩子表现出现过度负面的预期。

只要有好预期,平凡生也能成为资优生!?
那么对于孩子的预期是怎么产生的呢?心理学家曾对于我们思考的模式进行探究,发现人并不是一种理性思考的生物,常会为了节省认知资源(脑力),而有着反射性的自动化思考模式。这些思考模式很有可能是在物尽天择后人类潜藏在基因里一代传一代的能力。当知道了这件事情,回头来看,老师是人,照顾者也是人、所以总是无法如同机器一样始终用理性在面对孩子作分析应对,有时总难以脱离对孩子出现的自动化思考窠臼。对于照顾者来说,对孩子预期的形成,常是由孩子行为表现及生活点滴累积而来。
在面对生活点滴,当预期孩子表现时,由心理学家Kahneman和Tuversky提出的自动化思考“可及性捷思(Availability Heuristic)”成为第一个影响预期判断的角色。该角色让人对于容易想到的事情高估其发生概率的状况,也因此容易快速的影响到我们对于孩子判断。生活中孩子最容易被照顾者及老师挂在嘴边提醒或想到的,通常都是“他哪里做不好”、“他又打人/和人吵架”、“他今天又乱发脾气/大哭大闹”、“作业写不完”、“上课不专心”、“字写太丑”......等负面讯息,也因此,我们常会高估孩子出现令人困扰状况的概率,并且为之提心吊胆。
而紧接着由Wason于1960提出的另一个自动化思考“确认性偏误(confirmation bias)”角色,则扮演着让我们不断地搜集和孩子问题行为相关的证据进而重复强化我们对孩子的负面预期,因此好者恒好,坏者更坏,结合一开始的主角毕马龙效应的作用,从正向变成负向结果,形成孩子不断出问题行为的恶性循环。
可及性捷思、确认性偏误,两个造成误会孩子的狠角色
那么,我们该怎么调整对于孩子适当的预期表现呢?唯一最佳解答当然是“寻求专业讨论”,这也是为什么在早疗疗育或是处理孩子问题行为时,通常都会需要孩子先经过一系列“衡鉴评估”,而专业也会尽量避免在照顾者寥寥几句对孩子的描述就做出总结,避免可及性捷思狠角色的影响。
在经过各关卡以客观、经验综合形成的资讯,越丰富的资讯,越能贴近形成对孩子能力及行为表现的理解。针对孩子的能力、特质,过去经验、行为模式进行预期。然事事岂能尽如人意,照顾者身边不会永远都有个儿童发展团队提供24小时专业服务,那么,照顾者或重要他人该怎么调整自己对孩子的预期呢?